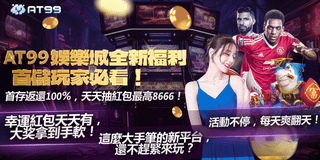賭博罪成立要件解析:聚焦「意圖營利」的司法認定標準
賭博罪概述與法律規定
在臺灣法律體系中,賭博行為受到《刑法》第266條至第270條的嚴格規範。賭博罪並非單一罪名,而是包含「普通賭博罪」、「圖利供給賭場或聚眾賭博罪」以及「發行彩票罪」等多種犯罪類型。其中, 賭博罪的核心構成要件 在於行為人是否具備「營利意圖」,此一主觀要件往往成為法庭攻防的關鍵。
根據《刑法》第266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同法第267條則規定:「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由此可見,法律對於單純參與賭博與 意圖營利而經營賭博 行為設有截然不同的刑責。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我國法律對「 賭博行為 」採取原則禁止、例外開放的立法模式,僅有公益彩券、運動彩券及在特定離島設置的觀光賭場(尚未實際開放)屬於合法範圍。因此,絕大多數的賭博活動都可能觸犯刑法的相關規定,而其中「意圖營利」要件的認定,往往決定了行為人所面臨刑責的輕重。
「意圖營利」的法律定義與判斷標準
「意圖營利」作為賭博罪的重要成立要件,指的是行為人主觀上具有藉由賭博活動獲取經濟利益的 直接故意 。根據最高法院判例見解(如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429號判決),此一要件不以實際獲利為必要,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有以此牟利的意圖即為已足。
在司法實務中,判斷行為人是否具備「意圖營利」通常會綜合考量以下因素:
-
抽頭金的收取 :這是最直接且明確的營利意圖表現。例如,賭場經營者從每局賭資中抽取一定比例作為場地費或佣金,此行為即明顯具有營利性質。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1234號判決即指出:「被告於賭博場所內,每局抽取一定比例金額作為頭錢,顯有營利之意圖甚明。」
-
經營規模與持續性 :臨時性、偶發性的賭博聚會與具組織性、持續性的賭博活動在認定上有顯著差異。法院通常會考察賭博活動的 時間長短 、參與人數多寡、是否有固定場所等客觀事實。如臺中地方法院105年度易字第1256號判決便認為:「被告提供住所作為賭場並持續經營達月餘,且備有專用賭具,足認其有營利之意圖。」
-
賭資流向與分配 :資金流是判斷營利意圖的重要依據。法院會審查賭資是否全部用於賭客間的輸贏分配,或有部分流入經營者口袋。實務上常見的「 水錢 」或「 洗碼量 」等抽佣方式,都是認定營利意圖的具體事證。
-
賭具與設備的專業程度 :專業賭具(如輪盤、百家樂賭桌)的購置與維護需要相當成本,通常非單純娛樂目的所能解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456號判決即指出:「被告購置價值不菲之電子賭博機台多部,顯非供一時娛樂之用,而係基於營利目的所為。」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地下賭場經營者為規避法律責任,會以「 單純提供場所 」或「 朋友間娛樂 」為抗辯理由。對此,法院通常會從客觀環境證據來推斷主觀意圖,如場所是否設有監視器、專人把風、兌換籌碼等專業化經營跡象,均可作為認定營利意圖的依據。
賭博罪其他成立要件分析
除「意圖營利」外,完整的賭博罪成立尚須具備其他要件,這些要件與營利意圖間具有相互印證的關係:
客觀要件:賭博行為與場所特性
依據刑法規定,賭博行為必須發生在「 公共場所 」或「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實務上對這兩類場所的認定相當廣泛,除傳統認定的公園、廟埕等開放空間外,即便是私人住宅,若容許不特定人隨時進出,也可能被認定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5898號判例)。
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 網路賭場 」的興起也帶來新的法律問題。我國司法實務見解認為,雖然網路空間非實體場所,但基於賭博網站的可及性與開放性,仍符合「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要件(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2154號判決)。
主觀要件:故意與目的
賭博罪除要求「意圖營利」外,尚須行為人具備「 賭博故意 」,即明知自己所從事的是法律所禁止的賭博行為。在一般參與賭博的情形(刑法第266條),行為人只需有賭博故意即可成立犯罪;而在經營賭場或聚眾賭博的情形(刑法第268條),則必須再加上「意圖營利」的主觀要素。
實務上常見的爭議在於「 社交性賭博 」與「 營利性賭博 」的區分。根據法務部(83)法檢(二)字第1123號函釋,親友間於年節時節以少量財物為注的娛樂活動,因欠缺營利意圖,原則上不構成賭博罪。然而,此一例外規定有其界限,一旦賭注金額超出社會通常觀念所能接受的範圍,仍可能被認定為賭博行為。
司法實務案例解析
透過實際案例分析,可以更清晰理解法院如何認定「意圖營利」這一抽象要件:
案例一:職業賭場經營案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1832號判決中,被告於工業區廠房內設置天九牌賭場,除提供專業賭具外,尚有下列行為:(1)每局抽取5%頭錢;(2)僱用專人負責記帳、把風及兌換籌碼;(3)賭場每日營業時間固定(下午2點至晚上10點);(4)廣告招攬不特定賭客。法院綜合這些事證,明確認定被告具有營利意圖,構成刑法第268條之罪。
案例二:網路賭博平台案
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456號判決涉及一個營運兩年多的線上賭博網站。該網站具有下列特徵:(1)會員制且開放公眾申請;(2)設有儲值、兌現機制;(3)網站從每注中抽成2%;(4)投入大量資金於網站維護與廣告。法院認為這些營運模式充分顯示被告的營利意圖,不因賭博發生在虛擬空間而影響犯罪成立。
案例三:家庭麻將爭議案
相較之下,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簡上字第45號判決則認定,親友間於家中進行的小額麻將娛樂,因具有下列特徵而不構成賭博罪:(1)參與者均為熟識朋友;(2)賭注極小(每底50元);(3)無任何抽頭行為;(4)純粹節慶期間偶一為之。法院特別強調,此類活動欠缺「持續性」與「營利性」要素。
這些案例顯示,法院在判斷「意圖營利」時,會全面考察 經營模式 、 組織程度 、 金流設計 等客觀事證,而非僅憑當事人主觀陳述。尤其當有證據顯示行為人從賭博活動中獲取固定收益或佣金時,營利意圖的認定幾乎難以推翻。
賭博罪的法律效果與風險防範
刑事責任層面
賭博罪的刑責因行為類型而有顯著差異。單純參與賭博者(刑法第266條)僅處 一千元以下罰金 ,屬於輕微犯罪;相對地,意圖營利而供給賭場或聚眾賭博者(刑法第268條),則可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刑度明顯較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賭博行為涉及 組織犯罪 或 洗錢 等情事,還可能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或《洗錢防制法》等特別刑法,面臨更嚴厲的刑責。例如,根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
行政責任層面
除刑事責任外,參與賭博者還可能面臨 社會秩序維護法 的處罰。依據該法第84條規定,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內賭博財物者,仍可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下罰鍰。這意味著即使賭博行為未達刑事犯罪程度,仍有可能受到行政處罰。
風險防範建議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應注意以下幾點以避免觸法:
-
避免參與任何有組織性的賭博活動 ,特別是那些設有固定場所、專業賭具及抽頭機制的賭局。
-
節慶期間的親友娛樂 應嚴格控制賭注金額,最好事先約定以代幣或極小額現金為注,並避免形成固定性的賭博聚會。
-
遠離網路賭博平台 ,這類平台通常設有複雜的金流系統,參與者不僅可能觸犯賭博罪,還可能涉及洗錢風險。
-
切勿提供場所供他人賭博 ,即便未從中獲利,仍可能構成刑法第266條的幫助犯。
對於可能涉及賭場經營的人士,必須認知到現今檢警機關多能透過 金流追查 、 通訊監察 及 大數據分析 等手段偵破賭博犯罪,傳統的隱蔽手法已難以規避查緝。任何意圖藉由賭博活動營利的行為,最終都可能面臨嚴重的法律後果。
結論與法律建議
賭博罪中的「意圖營利」要件,實務上係透過客觀證據來推斷行為人的主觀目的。法院會綜合考量 營運模式 、 金流設計 、 場所特性 及 組織程度 等多重因素,而非僅憑單一事證作成判斷。對於有意規避法律者而言,必須認清「意圖營利」的認定標準已日趨明確,任何僥倖心理都可能招致嚴重的法律風險。
從預防犯罪的角度,我們建議:
-
釐清娛樂與賭博的界線 :親友間偶一為之的小額遊戲應明確排除任何抽佣或經營性元素,並確保參與者的熟識關係。
-
認識新型態賭博風險 :網路賭博、電子遊戲場賭博等新型態犯罪已成為執法重點,其隱蔽性不應被誤解為合法性。
-
尋求專業法律協助 :一旦涉及賭博案件,應儘早諮詢專業律師,針對「意圖營利」等主觀要件進行有效辯護。
總而言之,臺灣法律對賭博行為採取嚴格立場,僅有少數例外情形得免除刑責。民眾在參與任何帶有賭博性質的活動前,務必審慎評估法律風險,避免因一時娛樂或貪念而身陷囹圄。守法自律不僅是避免刑責的最佳途徑,更是維持社會秩序與個人家庭和諧的根本之道。




![致歉[戰神賽特]正版機台火爆上線伺服器險些被玩家熱情擠爆官方緊急升級火速開放註冊全站首存紅利100%立即入場開局就有底氣](https://pimg.uk/unsafe/rs:auto:320:160:0/q:80/plain/https://www.at99cc.com/pimg/business/91/7185dbef/11b0/4036/8dd0/ff5fed9d286b.jpg)